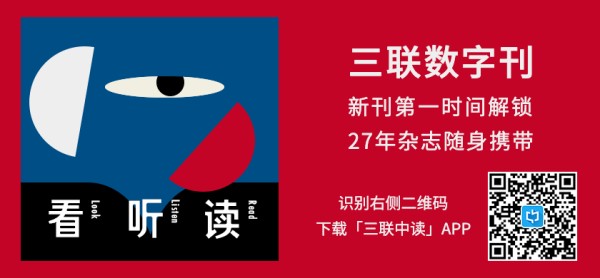“内心宁静有三种等级,生理上的宁静似乎是最容易达到的境界,印度神秘的修行者就曾经埋在地下好几天仍然活着;精神上的宁静,也就是消除个人的杂念,相对来说不容易做到;至于价值方面的宁静,也就是一个人没有贪念,只是单纯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一点似乎是最难的。” ——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誊抄《金刚经》
这天下午,韩馨逸买来食材,西丽堂壶馆的老板陈洋富下厨,几位好友以一席“鱼火锅”送别陈颖。陈颖是一位作家,笔名“湘夫人”。我们见到她,正是她要回浙江的前一天。她说自己仿佛是一只候鸟,每到冬天需要迁移,不然会冻死在香山,回来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鱼是陈颖喜欢吃的,她说自己“没有鱼,吃饭不香”。她是一位佛教徒:“开始信佛是小时候受外婆影响,但我不是一个精进的信徒,我不戒荤腥,但我不杀生。也许别人是在修炼,我更希望自己是在修行。‘修’难免本末倒置,‘炼’难免伤筋动骨,我个人修行的最高境界不是成佛,而是希望从静心正念开始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
陈颖当过教师、编辑、会计,还曾下海创业从商10多年。她说:“做自己想做的事,不问是劫是缘。”来香山前,她在中关村一家外资公司做编辑兼任出纳。她回忆说:“那时候每天十几个小时在电脑前,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到后来得了‘鼠标手’,手疼、头疼、肩周炎、颈椎疼,带病坚持了很久。因为一份信任,我可以为之卖命,虽然那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当这份信任缺失了,我就辞职了。机缘巧合,到了香山,一住就是6年多。”
“香山离闹市不远,这里是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在这里,她写散文、炒股票、学琴习画。她经常闭门不出,止语、禁食,用蝇头小楷抄写《金刚经》。她说:“香山的日子贫而不贱,高而不贵,我终于脱下了高跟鞋,换上了心爱的绣花鞋。”对于修行的法门,《天台小止观》讲:“具缘第一。呵欲第二。弃盖第三。调和第四。方便行第五。正修行第六。善根发第七。觉知魔事第八。治病患第九。证果第十。”而在陈颖这里,少了一份精进,却多一份豁达。能直观感受到的敬佛之心,就是那日积月累誊抄而来的厚厚一沓《金刚经》纸卷。

陈颖
陈颖告诉我们:“禅不可说,花开是禅,鸟鸣是禅,茶凉也是禅,我吸烟也能吸出一份禅意。”她在新书《一路寻欢》中这样写道:“喜欢香山的清幽,喜欢黎明时,翠鸟在窗外啼鸣的声音,喜欢闲暇时登高望远,忘了身在红尘,喜欢去山涧背点泉水,回家煮点新茶。”对于陈颖的“寻欢者”境界,画家崔自默评价道:“看破、放下、随缘、自在,知而弗行,但就着这点固执,得以走下去。”学者吴稼祥则认为她是:“求而不贪,憾而不嗔,恋而不痴。”一心向禅却不受拘束,这是陈颖追求内心平乐的修行方式。这应了《金刚经》的要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琴韵如来音
送别陈颖这天,孙雪华和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但晚上她并没吃“鱼火锅”就先回去了。孙雪华是一位古筝演奏家,她信奉“身空得健康,心空得自在”,曾经两次辟谷。她说:“禅修之后,朋友们都说我变了很多,越来越能放下了。毕竟还是俗人,对我来说,去掉分别心很难,但现在能让我心烦的事情真的少多了。”
孙雪华回忆说:“我爷爷是中医,做过皖西制药厂厂长,我爷爷的父亲做古筝、古琴。小时候一到过年,我的姑姑、叔叔就吹起口琴,唱《泉水叮咚响》和《北国之春》。你再看这古琴,体长3尺6寸5,相当于一年365天,上面有十三徽,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和一个闰月,有头有颈有肩有身有脚有尾,很像人形。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我从小就对佛啊禅啊国学啊这些很好奇。”
在名为“圣雅轩”的店铺里,桌上摆着古筝、古琴、笔墨纸砚,墙上则挂满了书法作品和汉服。聊得高兴了,孙雪华边弹边唱:“寒山鸣钟声声苦乐皆随风,君莫要逐云追梦,拾得落红叶叶来去都从容,君何须寻觅僧踪。”这首“呼吸便是梵唱,脉搏跳动就是钟鼓”的《寒山僧踪》,曾吸引了不知多少登香山者驻足聆听。“我这玻璃门就像一个慢镜头,往来疾走的行人临近我这里就慢了下来,很有趣。”孙雪华说,有一次她抚琴而歌,一位听众大姐激动而泣。在场的书法家肖作彪当即挥毫,写下“香山琴韵如来音”送给她。
孙雪华12岁学古筝,她说:“古筝明亮,是悦人的;古琴哀怨,是悦己的。我一般上午练书法,下午弹古筝,晚上弹古琴。有时同一首曲子我会根据心情变化来选择乐器。”
2003年,孙雪华来到北京。生活虽忙碌,却漂泊无依,直到2008年来了香山,她说才找到回家的感觉。“我和一个朋友来这里转了一圈,有雷音琴院,有香庐学堂,有香山画院,很喜欢,第二天就搬过来了。”吸引她的就是香山的文化氛围,新结识的朋友都热衷于探讨传统文化。在香庐学堂了解一段时间后,孙雪华对禅的兴趣更加浓厚,于是决定外出参禅。
2009年,她到扬州高旻寺“打禅七”。高旻寺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并称禅宗的四大丛林,所谓“打禅七”就是拿七天来用功。南怀瑾在《习禅录影》中讲:“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发誓若在七天之内不成道,不离此座。”高旻寺在禅修者心中具有相当地位,“仁文居士”赵文竹曾在此参加了12个禅七。孙雪华说:“我事后才发现,自己从北京到扬州的车票是10车厢10座,那天又正好是农历10月10号,这更坚定了我禅修的圆满之心。”回京后,她继续禅修,她在日记中这样写:“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也是生存之道,这一年的静修让我在精神世界的收获不少,真有点在寺院读博士的感觉。”
在演奏与书法之外,孙雪华还是个票友,自学了程派和梅派。她喜欢《锁麟囊》,因为这戏词中也蕴有禅意:“我正不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在香山画院,她和朋友们经常相聚合奏。赶上中秋、端午这样的日子,十余人扮上汉服,以古琴、古筝、笛、箫、葫芦丝、二胡等演绎《高山流水》、《梅花三弄》。孙雪华告诉我们:“我对禅的理解就是以出世的心态去做入世的事情。争取和执著是不同的,一个只停留在行为上,一个是心念上没放下。禅修以后,我放开心去做,争取而不执著。”
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