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新刊︱刘诗伟:创作是发现生活与发明生活
诗歌可以激发创造力,激发新的写作灵感 #生活乐趣# #读书乐趣# #诗歌鉴赏#
摘 要
Abstract
创作的基本问题是拥有怎样的生活与如何回应生活。抵达“生活的艺术”是困难的。真正的创作始于发现生活;发现生活以人为中心,发现的内容应当是具象的、深刻的、相对完整的。发现生活“依靠皮肤”感受生活。发现生活的同时与之后是发明生活(包括叙述形式)。文学作品或“艺术世界”是发明的产物。发明生活有四个艺术指标:独特性、审美性、自洽性与范式性。“艺术世界”实际是审美自由精神的体现。
“艺术源于生活”或者“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属于常识,无需跟作家多谈。这恰恰说明生活之于创作的重要。在一个正确的作家那里,创作永远是这样两个问题:拥有怎样的生活与如何回应生活。
生活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也包括与人类相关的所有事物,在文学这个行当通常叫“社会生活”,或“现实生活”或“时代生活”。虽然社会生活由无数个体的活动组成,却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个体活动的相加与汇合,关键与重点在于各种个体活动之间所发生的联系或形成的关系,在于联系或关系中的机理——由前因与后果、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内在、时间与空间、正面与负面、疑难与趋向等因素“化合”的逻辑。生活无边,复杂深刻。现实里,人的生活(存在)出于本能与自觉,其活动具有自发性、趋利性、常态性、动态性与开创性,总是尽心而为、拼力而行,实际上人类(以及相关事物)一直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共同实现或创造社会生活(包括理想生活)。由此得见,任何作家个体创造的生活注定少于和小于人类的整体生活(独特性除外),反而是社会生活成为所有个体艺术创作或文学创作一直在努力企及的对象。所以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说:“一切艺术都是为了反映最大的艺术,即生活的艺术。”
一、有效创作的起点:发现生活
有效创作始于创作者发现生活。
确认发现生活之于创作的起始意义基于艺术实践的逻辑。布莱希特正确而笼统的原则——反映“生活的艺术”——难以操作,只能拿它作为创作的“战略指导”,另辟“单兵突进”或“以点涉面”的路径回应并抵近“生活的艺术”;与此同时,生活固然永续不竭,但生活一直在被文学开采和反映,生活中满眼皆是“红海”似的公共知识,几乎不会自动冒出一片未被他人经营的“蓝海”等候作者,而创作遵循新奇或新颖的文学原则,不可以贩卖陈旧的或一般化的生活,必须奉出确有新意的东西;如此,创作的出路就是一条路——发现生活。只有从生活中发现有新意的生活并加以反映和表现才是值得的、有效的;反之,书写人所共知的或已被反映的生活则没有意义。米兰·昆德拉谈论小说的艺术时说:“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的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发现”是小说的“道德”。事实上,发现是所有文学的道德。可以这样理解发现的价值:创作与创新同在,创新与新颖同在,新颖与发现同在。所幸生活不死,生活永不停歇地孕育生成新的生活(包括知识增长);回应生活的文学,永远不缺发现生活的机遇与可能。
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发现。发现最怕像无头苍蝇一样嗡嗡乱飞。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发现必须以人为中心,围绕人感知生活和拣拾新素材新信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地发掘新意思新价值——这是认识论的基本方法。
而且,发现的内容应当是具象的和相对完整的。主要如下:
一是发现新生活与新现象中的新故事、新人物。有一个20 世纪70 年代末期的案例:短篇小说《班主任》之所以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打响第一炮的作品,是因为作家刘心武在时代的“伤痕”中,及时发现了“内伤”故事;作品通过描写一群中学生读过外国小说《牛虻》后的争议及其它,成功刻画深受“极左”思想毒害的女生谢惠敏的扭曲的“正派”,在当时产生了超出文坛的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反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及21世纪初,湖北作家以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为特征的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同体裁作品中出类拔萃,其共同的方法是发现新故事与新人物,比如刘富道的《南湖月》、王振武的《最后一楼春茶》、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楚良的《抢节即将发生》、李叔德的《陪你一只金凤凰》、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刘醒龙的《凤凰琴》、叶梅的《五月飞蛾》、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等。不必怀疑新生活新现象背后蕴含着新故事、新人物与审美新意。在今天,躺平或内卷的新现象必有深刻的生活逻辑,关键是在现象中发现新故事(情节),在新故事中发现新人物,让二者照见生活本身发生的某种“艺术”。
二是发现新人物的独特情感、独特思想、独特行为与独特命运。独特,指将要表现的东西不曾被表现过或不同于以往任何艺术形象。没有独特的东西不能成其为创作。人都有基本面,人的性格是圆形的,创作必须在“基本面”之外或“圆形”之中找到人物独有的典型的那一点或那个部分——前面说到的谢惠敏的“扭曲的正派”就是“那一点或那个部分”的体现。经典文学人物如哈姆雷特,他的仇恨、悲思、痛苦、证罪、决斗、复仇、死亡等,因其身份,因其遭遇的事件以及事件中各种人物的特殊牵扯,全都带着非凡的元素,只为他独有,他便因此成为独具艺术感染力的典型人物;而此中,即便书写独特情感和独特思想,也不是抽象表述,而是寄于具体情节、细节与行为,用丰盈且匹配的语言形象加以显现的——因为文学只能是具象的。
三是发现新人物与生活环境的独特关系。生活环境是广泛的,是现实里与人相关的具体事物,既包括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也包括由家庭、单位、组织、朋友圈以及制度、经济、科技、历史、教育、宗教、风俗、文化、自然之因素而融合的社会背景。人是环境塑造的,环境是人物的根据;找到人物的环境根据,结合环境塑造人物,同时用人物映照环境——这是创作应有的考据与文学应有的指标,也是作品意义的扩张。一般来说,生活注定存在不如人意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部分,人注定要冲撞、反叛和改造“死猪”。清末明初的那个阿Q之所以耐人寻味,不单因为他是一个映照环境的可怜的“顺民”,他到底有反抗,只不过他的反抗是以“精神胜利法”表现出来的,他是环境的产物又印证了环境。
四是发现新人物的新的存在性与人生况味。存在性是一个现代意识,是文明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觉悟。所以存在性成为了文学的一个向度。由存在视角发现人的新的存在,必然获取超越一般社会意义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在存在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必然在传统审美中注入新的情感、理性与认知,带来深刻、浑厚而悠远的思想意蕴。从文学角度看,存在性的发现更接近生命本质与自然真理,特别需要创作的精进与拓展。在卡夫卡的《变形记》里,靠推销养家的萨姆沙变成了甲壳虫,父亲用苹果砸他,母亲吓晕了,妹妹对他很厌恶,他只好远离,在孤独、饥饿和内疚中死去:这便是一种荒谬无奈的人生、一种存在性的况味。习惯了传统文学又缺乏生活新感受的作者与读者在这方面会迟钝一些。
以上是具象发现生活的四个方面——生活是无边的具象。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现生活的多少与深浅决定作品高下。
不用说,发现生活要到生活里去,在感受、认知、积累与想象生活过程中发现生活。作家作为生活里的角色直接感受生活是最能发现生活的,而且这样的发现最为亲切、鲜活、丰赡、靠谱: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海明威、加缪与马尔克斯是这样的作家,鲁迅先生是,萧红是,柳青是,王蒙也是。作家的确都有超常的敏感,但敏感毕竟离不开具体生活;而且,发现的多少与深浅和感受生活的时间长度与进入深度密切相关。阿·托尔斯泰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果真如此而不死,对于创作是一种幸运,因为占有非凡的生活素材实属创作机遇,有志向的作家倒是十分需要经历“三个三次”的运气。
另一个稳妥的途径是用心收集和消化生活素材。浮士德是早于歌德的民间传说,但歌德创作了《浮士德》;现在去德国莱比锡旅行,导游会指着集市广场的歌德塑像,给你介绍歌德在莱比锡大学念书时遭遇失恋和搜集浮士德素材的文青岁月。蒲松龄也是下得本钱的,为了创作聊斋,在路边支起茶摊,凡给他讲了好故事的人,可以免费喝茶。民间故事之所以被传讲,是因为总有吸引人的意趣,对于创作几乎是半成品。当然,在收集素材时免不了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智识。
也有特例。有一类作家,极少的一类,他们较少在社会生活的一线或漩涡中扑腾,缺少直接的一手生活经验(未见他们拿出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作为创作题材),但他们的触觉之灵敏与想象之发达是卓越的,对于生活,他们不需要太多“大段大块”的现场感触便可获得新的丰饶的感知;他们用一只强大的胃消化来自书斋或书本的海量生活信息,他们善于在汇总融合那些间接生活时发现生活,并创作出别有意趣的作品。20 世纪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中国当代的李敬泽是这样的例子:博尔赫斯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曾任布宜洛斯艾利斯市公共图书馆馆长;李敬泽一直是文学领域的专职工作者,长期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二人常常从书籍中跑进生活的实境,跑向奇妙的境界。网络文学塔尖上的那几个人也属于这类作家。不过,这种发现生活的方法显然不宜普遍借用。
发现生活当然不是像老鹰一样地站在某处用眼睛盯着生活。雨果曾说:富人凭借客厅的寒暑表判断冷暖,穷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皮肤去感受”。“依靠皮肤去感受”就是让自己直接融入生活——做生活中的“穷人”是作家的宿命。发现也需要眼力。作家的眼力除去活跃于右脑、神经、心灵、荷尔蒙中的先天的特殊因子,主要取决于后天的经验、知识、思想与脑力。作家必须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专家,拥有无人匹敌的生活见识。其他相关的知识结构也应当是健全的,比如,知道文学迄今为止都写了些什么,判断自己的发现是否属于有效的发现。作家除非搁笔,一生都在读两本书:文字的书,生活的书。对于作家而言,没有白过的生活,没有多余的知识。但主要的知识是围绕人的,发现生活的实质是发现人。

刘诗伟
二、有效创作的过程:发明生活
米兰·昆德拉认为:文学是超越道德的,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和小说形式创新的可能性。
我们不必为“超越道德”的说法惊慌起哄,此处的“超越道德”是指叙事上撇开道德中心,强调回应生活的创作不要被既有道德(包括不合适的人际规约或准则)所桎梏和牵扯,而应当致力于探寻和表现人的存在,在存在中照见更合理更文明的人伦;这样的“超越”正与昆德拉所主张的文学意义——文学的目的是要抵制和排除不适合人类生活的东西——互相呼应。任何时候,现实生活都不可能完美得没有“不如意”“不适合”的东西,昆德拉是要为文学创作清除思想的羁绊并打开探索的疆界。
不单小说的唯一使命是探索——所有体裁的文学都一样。
依据探索论,文学创作自然应该有所发现,或者必须有所发现;尤其是,这种探索明确指向现实中暂未被发现的或尚不存在的两种“可能性”——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与小说形式(文学形式)创新的“可能性”。“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呢?显然,除了可能发现的东西,就是发明的东西了——因为“可能性”不是现有的生活存在与既有文学已经表现的生活存在,也不是已经出现的一切叙述形式,而是“可能”更符合现实生活与自然律动的存在,以及“可能”与之更匹配的叙述形式。这是创作探索的基本逻辑。
那么,“可能”的生活即发明的生活——创作就是发明生活。
如果把发现与发明结合起来:发现生活是发明生活的前锋,发明生活是发现生活的扩张;此间,发明生活自然而然地包含着发明作品的叙述形式——理由是,新的生活必然自带新的形式,或者新的形式只能存在于新的生活之中——这一点也恰好符合了布莱希特的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
至此可能仍然让人忧虑:以上结论仅仅基于昆德拉个人观点的推演。的确,昆德拉的文学实践放弃“整体中的确认”,既不能用它否定他之前的那些经典作品,也不能用它规约他以后的所有创作——但他的作品是杰出的一种,他在理论上关于“探索”“发现”以及基于二者的“发明”的观点,无疑属于“通适”的文学事实,是真知灼见。况且,这里所以征用昆德拉的说法来表述创作是“发明生活”,不过是为了方便快捷。实际上,经典文艺原理中由日常“感官世界”到“艺术世界”的论述早就深蕴“发明生活”的创作论——只是没有使用“发明”的说法,而历来的经典作品皆可为之佐证。
创作最终要把发现与发明的生活变成文学文本——语言的“艺术世界”。这个语言的“艺术世界”在现实的感官世界里找不到,在过往的文学作品中也找不到,是一片想象的全新的独立的独特的浓缩的自洽的富有审美意蕴的生活。它是现实生活溢出或逸出的艺术生活,以文学性为旨归,只要符合文学性,无论文本体量大小,都可以称之为“艺术世界”。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甚至不是单凭从生活中发现的许多的闪亮珠玑码成的,而是内容与形式融合的一种整体的结构性的发明创造:除了最初的发现、发明与构想,整个创作过程一直都在再发现、再发明与再构想;除了可以借鉴的文学形式、方法与技巧,关键在于用新的语言形象去粘合、装置、表现和构建文本——实现昆德拉所说的“形式创新”。
在语言的“艺术世界”里,有专属的人物、故事与环境,有独特的天地、山川、光亮、树木、屋舍、人与人、鸟与兽、花与草,有不一样的色彩、声响、温度、气味与气息,有氤氲各处的活气,有典型的世相、命运与悲欣,更有持久诱人的情感、趣味、思想、品格……一切都是未曾见过的天然,进入其间可获得绵密的审美愉悦。这个“艺术世界”的确是想象的,是想象让发现与发明持续开枝散叶,发育成“艺术世界”。不过,发现与发明也有理性思维的成分,创作中,想象一面携带发现与发明前行,一面自有发现与发明的功能,加之作品形象的自发性生长,实际上,想象、发现与发明、作品形象三者处于互动相生状态。如果说创作过程就是想象过程,想象以发现与发明为目的,同时受其指引——这种复杂的心理运动体现了创作的难度与奇妙,也是文学价值(或有效性)之所在。
诚然,发明生活如同发现生活一样是具体形象的,二者涉及的生活形象重叠而纠缠,但其实各自的表征不一样——发明趋向整体,发现相对零碎零散。发明生活的具体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粗粝闪光、零碎凸显的生活素材之间建立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一是实现缜密完整、具象生动、别有格局的文本形式。在过往的文学言说中,一般用神话、寓言、童话、志怪志异、科幻、悬疑、穿越、架空之类来解释“发明生活”或“艺术世界”,而对于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则因为“真实性”理论的蒙蔽,使“发明生活”跟“再现现实生活”发生龃龉,或者似是而非——这是来自旧知识的误会。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神话与穿越之类毕竟往往只是甜点,日常正餐和大餐还是直面现实“发明生活”的文学。整体而言,“发明生活”的创作更多聚焦于现实生活。
从发现生活到发明生活,到实现语言的“艺术世界”,是遵循文学性的创作活动。文学性对创作的指引与规约系统而明确,落实在“艺术世界”或具体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四性”:独特性、审美性、自洽性、范式性。此“四性”是“发明生活”的艺术方向与文学指标。
(一)独特性。“艺术世界”的生活是独特的:作家针对有所发现的素材,进行想象发明,辅之以概括、提炼、加工、装置、修辞等艺术处理,让新的人物、故事、情节、环境、情感、思想等更为凸显,更加典型,从而生成一种艺术的陌生的独特的语言化生活。创作天生听从独特的召唤。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那个马贡多小镇的生活故事实在太特别了,评论家一致指认它是魔幻现实主义,称赞作家是热衷于制造魔幻的高手;实际上,马尔克斯说他所写的都是从现实生活里发现的,包括那片载着雷梅黛斯飞上天空的床单,在现实中,是一对父母为掩饰女儿不光彩的出走而无奈编制的一个说法,因传说得久,竟让人们带着善意予以默认——被“事实”了。及至创作《百年孤独》,深感人世孤独的马尔克斯对这个发现颇有感触,进行艺术利用,方才发明了这个独特故事。再读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你会深陷于一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实有的艺术化的独特生活及景观之中,但它又那么真切——那是福克纳的发明。
(二)审美性。现实生活蕴含审美,但不会宣示审美,审美是艺术与创作的核心功能。即便提供了独特故事的文本,如果其中缺乏审美态度,没有审美意味的贯通和浸润,必定缺少魅力与感染力,必定是半死的、非艺术的、与文学性不相干的东西——犹如新产品说明书,它只能传达信息或知识,不可能为阅读带来审美愉悦。创作中,审美与发明生活始终在一起,或运行于发明生活的全过程,是创作背后的精神动因与动力,也是发明生活的诉求之体现与价值之所在。在杰出作家那里,审美潜伏在主体精神中,而发明生活意味着发生审美,意味着二者同理共情与互动相生。莫言在《蛙》里写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一生,不是一般化礼赞接生或探讨计划生育方略,而是透过特定背景下的接生故事,拷问时代、生命与人生,其间流淌的乖谬与无常便是作品不凡的审美倾向。一部作品,如果没有审美,就是一摊杂货,即便是“奇巧”的杂货也没什么意义。没有审美的发明不是发明,不是艺术。审美也不是附着物,而是融入在叙事与形象里;有时不着表情,有时可能是反表情的表情。
(三)自洽性。作为发明生活的“艺术世界”,应当有一个融和自然逻辑、生活逻辑与艺术逻辑的自有逻辑,这个自有逻辑让“艺术世界”具有自洽性——即作品内在和谐、独立完整、恰到妙处,尤其是让那些在别处几乎不成立的事情(人物、故事、情节、细节、情感、环境等)在这里反倒是“合榫”有效的,同时对所有“不合榫”的东西具有排他性(即通常所说的“割爱”)。自洽或自有逻辑是具体“艺术世界”的特定的生态律。特定生态容纳特定人物与事件,采用特定的叙事与修辞,生成特定的情思与意蕴;反过来,特定的人物、故事、叙事、修辞、情思与意蕴也让“艺术世界”形成特定生态。自有逻辑是创作主体的艺术思想在具体作品中的反映或实现,是理性与想象的有机互动与互治。自洽性没有定式,原则是让全部叙事或书写趋向恰当和谐的审美极致;在文本体制与体量方面,以思想意蕴的最佳发生、发展、完成为前提,每个层次的叙写不可以随意堆砌或有所欠缺,必须行止有度,只为达至艺术高点;不然,作品就成了一个漏斗或仓库,比如写孤独的小说,要么把孤独感写“漏”了,要么写成堆积孤独故事的仓库。自洽性是“艺术世界”的生命线。在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那些贫穷、奔走、征寻、孤寂的人,只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出现,只在自洽的“艺术世界”得以存在。
(四)范式性。范式是从科学理论里拿来的一个名词,原指科学理论体系,是由理论、定律、应用、工具等内容所形成的被普遍认同的科学研究的模型,也叫范式或模式;拿它来解释“艺术世界”,不是要求新的“艺术世界”(作品)符合某一种既有范式,恰恰相反,是强调任何一个“艺术世界”都应该成为一个独立范式——范式的“这一个”。作品范式由叙事、语言、人物、环境、意蕴、结构、节奏、色调、体制、风格等因素融合而成,独特而自洽,以整体艺术成就超越同类(题材与体裁相同)作品为指标——其超越的程度即范式性。范式是唯一的,比如《复活》与《阿Q 正传》;而且,作品卓越的范式一旦存在于世上,是不可复制的模型,复制者亡。发明生活的“艺术世界”具有这样的范式才称得上高级。中外文学的任何一部经典都是范式,后来的创作者读过之后只好羡慕或嫉妒地绕开去,如果在方法或思想上明显得了启示与借鉴而创作作品,也要赶紧声明向某某致敬,生怕被人看作小偷。
发明生活是无穷尽的,因为艺术与生活的意味无限。
再举一个“发明生活”的例子。有一篇日本短篇小说《最后的看客》,大约写于20 世纪中后期,作者跟这篇小说一样名气不大,叫生岛治郎。作品写一个民间艺人川崎大八(艺名竹山)的生活与命运。出演配角的竹山执着于“悠哉舞”,而这种舞蹈在艺术市场正在无法挽救地式微;中国和别的国也有人写类似的题材,一般也写得出凄哀幽怨,但均不及这个作品震撼人心。看看《最后的看客》发明的“艺术世界”:在一间住宅的仓房,吊死的竹山在风中摇摆,晃晃悠悠,恍如“悠哉舞”,此时仓房里没有看客,只有老旧器物和一只上吊后斜倒的木凳……仓库是大儿子家的,竹山生前住在大儿子家里;在外工作的二儿子川崎二得悉父亲的死讯,悲伤回忆父亲过往的生活情景,赶回家安葬父亲后,想侦查父亲何以自杀,他走访了几位父亲生前的同行与朋友,从父亲晚年艰辛而卑琐的生活中似乎感觉到父亲自杀的缘由……然而,惆怅的川崎二来到父亲自缢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些焦糖滓,想起父亲在日记中写过为智障的小孙女由佳熬制焦糖,恰在这时,小由佳冲向他,叫喊“叔叔,悠悠”,并手指木凳,为了满足智障的小侄女,他莫名地登上木凳,把自己吊在房梁上转起圈来,双脚随之忽上忽下地跳舞,小由佳即刻开心得咯咯笑……原来父亲的知音是这个智障的小由佳,小由佳竟是父亲最后的唯一观众——而父亲不是自缢,是为了让小由佳看表演高兴而不慎缢死的。作品在叙事中推理,以推理带动叙事。这篇小说被收入中文版的《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虽没有名气,却是一篇可以与任何一流短篇小说媲美的杰作,因为它的独特性、审美性、自洽性与范式性都是一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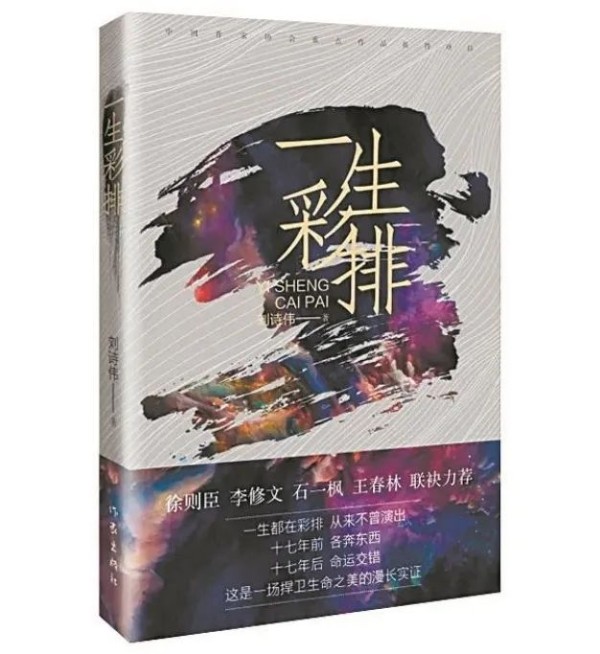
刘诗伟长篇小说《一生彩排》
三、“艺术世界”与自由精神
人类为什么需要“艺术世界”?因为那里有自由精神。
现实生活永远存在“不如意”“不适合”的东西,包括实现个人意愿的不自由;虽然不能简单笼统地说“艺术世界”比现实生活更高、更理想、更完美,但它毕竟可以发明或重新装置一份如意的生活——让这份生活更新颖、更集中、更浓缩、更生动、更典型,从而以审美方式摆脱或抵制“不如意”“不适合”的东西。这种“发明”与“摆脱”便是向往更高、更理想、更完美、更自由之生活的自由精神的实现。如果说文学发明的“艺术世界”是“应然”的,实际上是创作主体的审美“应然”——通常不必做科学的实证。
由于“艺术世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审美诉求,发现与发明生活的创作想象注定要响应心灵的跳动,回应心中的“块垒”,忠于对生活的认知与态度,听从真理与艺术的召唤——保有审美的自由精神。也正因为此,文学在面对和书写当下生活、过往生活、未来生活时,才有千差万异的“艺术世界”或审美表现。
只不过,创作者有必要明白,基于文学性的指引与规约,审美的自由精神实际已找到若干发挥的通道,或者已经可以分出几种主要的类型——这一点,既可以帮助克服茫然也能启发创新突围。具体如下:
其一,表达向往与追求。面对“不如意”“不合适”的生活,在表达愤慨之际,着意表现理想生活,代偿创作主体的向往与追求。杰出浪漫主义诗人是这方面的高手。屈原写《离骚》,既有“哀民生之多艰”“众女妒余之峨眉”的批判,也有“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李白厌恶“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世态,向往“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畅快人生;“五四”时期郭沫若创作《女神》也属此类。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永动机,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只是到后来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传统的理想生活的图景几乎被使用光了,没法一直炒现饭——浪漫主义主要作为一种精神原力在所有创作中运行。
其二,表现纯美与诗意。向着“不如意”“不合适”的生活转过身去,投入不在眼下的——实际也是想象的——圣洁、适意、美好而迷人的生活。纪伯伦、泰戈尔在这方面是开拓者与领袖,“五四”作家冰心受影响最深。沈从文在社会动荡不安的1934年写《边城》,极力写出边地诱人的风土美与人性美,读来让人觉得人生还有美好活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写疯子小偷的纯美。日本的川端康成撇下“不如意”“不合适”的生活,沉迷于“新感觉”的生命之美。川端康成曾明言:他所写的是生活中不曾得到而心中想要的生活。不过,这类创作的生活面很窄,内容不显波澜,需要对人物做内在细微的表现,创作的难度或许更大,实际存留的经典作品较少。此外,在当代一些评论家眼里,一般以为这类作品缺乏现实主义的厚重与勇猛——这应该是一种成见。
其三,探向本质与真理。关注人生本质需问津哲学。这类作家对生活的感知之敏锐之丰饶之深邃是一流的,理性思维是超一流的——而理性一旦运转起来便持续运转,不断拷问和探究生活;他们看穿了过往文学对“阴暗”“丑陋”或“不如意”“不合适”的生活的表达,发现了生活的演进,在生活感知中加入理性思考后,努力寻求认知的突破——创作中的发现与发明不再受到过去思想模式的召唤与制约,而是锐意开发新哲学,或接受新哲学的指引与帮扶,比如加缪,发明了“局外人”的“艺术世界”,表现存在性荒谬。这类创作的麻烦在于形象与理性不太好融合。老派作家大多不做这种尝试,因为理性或思想资源比较薄弱、偏执、老旧,也缺乏把理性融化到形象中去的艺术经验与才能。
除了以上三种,神话、寓言、科幻、仙侠、穿越、反讽、荒诞、宗教化、神秘化、黑色幽默、元叙事等,也是释放自由精神的审美方式。网络文学在某些层面充分表现出审美的自由精神,仿如一股清风。顺带的问题是,为什么理想生活无法在文学作品中独立整全地描绘或呈现?这是因为涉及理想社会的模式问题和服从审美效应;童话、科幻与田园诗似有直接表现的尝试。
创作的自由精神反映在杰出作品的“艺术世界”里,也体现在杰出创作的活动中——没有自由精神,没法正常感受生活、发现生活、发明生活,遑论创作想象。精神自由总是让作家莫名地才华横溢。作品脍炙人口的斯蒂芬·金说:“世上没有点子仓库,没有故事中心,也没有畅销书埋藏岛;好故事点子真的来自乌有乡,凭空朝你飞过来;两个之前毫不相关的主意碰到一起,青天白日里就产生出新东西。你的工作并不是找到这些主意,而是在它们出现时,能够认出它们来。”如此,便是处在“发现”与“发明”的自由王国。
毫无疑问,发现与发明生活的创作——需要创作主体始终对生活充满激情与智思。除非刻意掩饰心中大海一样的波涛,或者创作处于火山爆发前夕的静默状态,一个冷漠而思想贫乏的人,对生活是鲜有发现与发明的,即便给出了发现与发明也是干瘪枯燥的。关于激情,不否定sexuality(性)与appetite(食欲)的本能冲动或潜在诱发,但杰出作家总是善于把这两样安顿在合理的居所,不断发育博爱、关切、同情、悲悯、洞彻人世的情思——在感受宣泄心头块垒的愉悦中,致力于奉出不同凡响的于文明有益的“艺术世界”。
责任编辑:叶 李
原标题:《《写作》新刊︱刘诗伟:创作是发现生活与发明生活》
阅读原文
网址:《写作》新刊︱刘诗伟:创作是发现生活与发明生活 https://www.yuejiaxmz.com/news/view/577913
相关内容
宁静论文范文 生活是严肃的,艺术是宁静的有关论文写作资料现代散文诗写作技巧
《生活教育》期刊
重磅!亲子手工活动:陪孩子发现生活中的诗情画意
【描写宁静平和的唐诗或古诗有没有描写社会生活宁静平和的唐诗或
让写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人间有味是清欢”|在诗词中,发现真正的精致生活
在生活现场凝练美好的诗意
创新与生活作文
空调:最伟大的发明,也是最让人疲惫的发明

